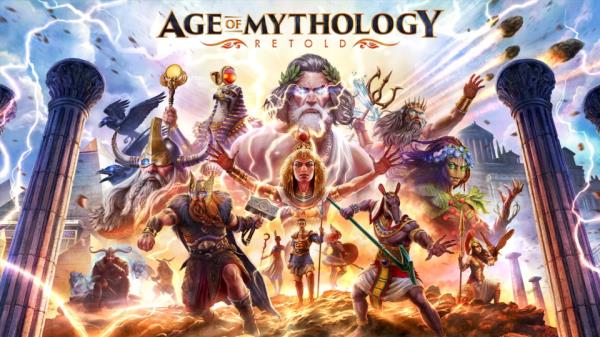Janet Maher在加沙报道。
加沙浸信会前埃及牧师的巴勒斯坦妻子与她的三个孩子和其他350人一直在圣波菲利斯希腊东正教教堂避难,但她的丈夫没有。在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的两周前,汉纳·马赫(Hanna Maher)暂时回到了埃及,战争爆发后他不得不留在那里。
尽管像CT之前报道的那样,她独自遭受了43天的轰炸,但家庭分离是珍妮特和她的孩子们现在安全地在埃及与汉娜团聚的原因。但首先,他们必须经历一段痛苦的旅程,从含泪告别一个神圣的社区开始。
珍妮特说:“我和这些人呆了几个星期,这种经历让我很伤心。”“但每个人都恳求说:如果你出去,就把我们的情况告诉全世界。”
加沙地带卫生部11月10日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加沙地带的死亡人数超过1.1万人,其中包括5000多名儿童。但是,除了弹片和散落在教堂围墙上的人类尸体残骸外,里面的基督徒对这一切知之甚少。
没有电视,没有互联网,只有断断续续的手机网络连接,珍妮特和她的加沙同胞们每天只知道战争的现实。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想办法弄到食物,年轻人的任务是去外面的当地市场。
通常情况下,这一天会以轰炸开始——让人们从窗户和门跑到房间中央。牧师每周三次主持晨祷。经常,他们会聚集在一起即兴唱歌,只是为了平息他们紧张的情绪。有些人会读圣经;其他人则独自坐在长椅上哭泣。
他们会经常打扫。每次爆炸后,灰尘和碎片都落了下来,而大多数人都患上了某种疾病——咳嗽、发烧、胃痛——到处都是苍蝇,从街上的尸体上飞来飞去。
由于没有早餐或晚餐,大多数日常膳食都是扁豆汤,偶尔会有米饭或通心粉。水很少是干净的,尽管神职人员通过向附近的清真寺出售汽油来获得一些水,清真寺用汽油来运行抽水发电机。
“有一次,牧师还能找到巧克力,”珍妮特说。“就像圣诞节一样。”
但在下午4点左右吃完东西后,夜幕降临了。没有电,每个人都搬到床垫上,断断续续地睡了一晚。当其他100人在教堂的葬礼大厅睡觉时,珍妮特给她的孩子们读了诗篇第23篇。但她依靠诗篇91中更为激进的现实来解决自己焦虑的想法。
“一千个人倒在你身边,一万人倒在你右边,”珍妮特背诵道。你若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又以至高者为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棚。
她有丰富的个人经验来证明这一点。
在把她的家人搬到避难所之前,珍妮特离开了她的公寓去寻找食物。在市场上找不到,她就回家了。五分钟后,一枚导弹击中了该设施,杀死了她的邻居。这场悲剧深深震撼了她,她也看到了上帝之手在保护她。
但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即使是在教堂里。以色列国防军(IDF)说,一枚以色列导弹袭击了附近的哈马斯指挥中心,击中了教堂外,造成至少20人死亡。上周,一名老年男子因治疗胆囊的药物用完而死亡,一名年轻人因严重发烧而无法前往医院。
为了寻找哈马斯劫持的人质,以色列军队袭击了附近的希法医院。
这一消息促使在马希尔之前担任加沙浸信会(Gaza Baptist Church)牧师的巴勒斯坦人汉纳·马萨德(Hanna Massad)向在圣家族天主教堂(Holy Family Catholic Church)避难的两位教会长老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几乎每天都与他们保持联系。当问及两名基督徒每周去希法三次做肾脏透析时,他得知他们为了寻找一家正常运转的医院而搬到南方。
尽管医生和药剂师在教堂避难,但那里的一位老人去世了。
“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糟,”马萨德说。“如果你得了重病,你很可能会死。”
内心的生活充满了忧虑——但也充满了鼓励。他说,教堂里比外面稍微好一点,每个人都试图互相帮助。他们已经采取了诺亚方舟的地位,马萨德继续说。虽然暴力的波浪拍打着他们的船,但他们感到被耶稣的宝血保护着。
这是珍妮特使用的同样的类比,但用途不同。她说,一旦方舟安全着陆,他们所能找到的只有死亡和毁灭。她一直在给避难的孩子们讲《圣经》故事,并没有得出那种病态的结论。她说,约伯失去的一切后来都被上帝恢复了。
但私下里,她觉得自己是约伯的一个朋友。她想,也许加沙的毁灭是上帝对基督徒缺乏精神奉献的惩罚。不,有时候事情就是发生了,她责备自己。当你感到恐惧时,不要担心该怪谁。
现在在外面,她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
“以色列和哈马斯都不关心我们,”珍妮特说。“穆斯林和基督徒没有任何罪行,无辜的人正在死去。”
以色列则不这么认为。珍妮特的哥哥是几个接到以色列国防军电话的人之一,以色列国防军告诉他们到南方去寻求安全。她说,这条信息带有半威胁的意味:如果哈马斯的任何人进入教堂,教堂就会被炸毁。
无论如何都无法入睡,圣波菲里乌斯的基督徒设立了夜间守夜活动。有一次,清真寺里的穆斯林过来帮助他们赶走了几个试图强行进入的陌生人。在其他情况下,他们击退了偷窃的企图,因为饥饿的人认为基督徒可能比他们有更多的食物。
一些穆斯林继续在教堂内避难,因为教堂与邻居分享了它所能分享的东西。
然而,宗教兄弟会主要是地方性的。珍妮特的哥哥告诉以色列国防军,基督徒在南方没有亲戚,也没有教堂接待他们。她指出,南方的穆斯林妇女会遮住头发,那里的男人几乎没有处理其他信仰的经验。
据说,狂热分子在首都加沙城外有更强大的根基。
“他们不会杀我们,但他们不理解我们,”珍妮特说。“这是一种不同的文化,我们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反应。”
加沙的基督徒大约有1000人,大部分住在这三座教堂附近,都在首都。2007年,哈马斯占领了这片沿海飞地,同年4月,这个当时约有7000人的社区在巴勒斯坦圣经协会遭遇炸弹袭击,10月,该协会书店的经理被谋杀。哈马斯谴责了这些事件,并承诺进行调查,但没有人被绳之以法。
到2012年汉娜成为牧师时,基督徒人数已经减少到3000人左右。2020年的一项跨巴勒斯坦调查发现,考虑移民的基督徒中有60%是出于经济原因。虽然只有7%的人提到了安全状况,但77%的人担心严峻的萨拉菲派穆斯林的存在,69%的人担心哈马斯等武装派别。
但83%的人担心被犹太定居者赶出家园,而62%的人认为以色列的目标是将基督徒赶出家园。
不知怎么的,这些都没有影响到她的孩子们——10岁的马修、9岁的纳塔莉亚和5岁的蒂莫西——甚至在爆炸期间,她把他们的床垫从窗户上移开。
“除了我的孩子们,没人能睡得着,”珍妮特说。“我对他们的平和感到惊讶。”
她说,最小的儿子有时会感觉到母亲的恐惧,就拉着她的手提醒她,上帝会保护他们的。
与此同时,他父亲一直在打电话。
在与埃及驻约旦河西岸首府拉马拉大使馆的联系中,汉纳还敦促埃及尼罗河长老教会代表他的家人进行调解。加沙和埃及之间的拉法边界暂时开放,允许一些人离开,但当它再次关闭时,他的希望再次高涨。但这项任务很复杂,因为他的孩子们有埃及公民身份,而珍妮特没有。
上周四,她收到消息,她的三个孩子都在撤离名单上。第二天,她和父母一起出发前往边境,因为她的母亲——在加沙的土耳其医院接受治疗的癌症患者——被承诺由珍妮特的父亲陪同转移到土耳其。
那天晚些时候,珍妮特得知她的名字也被列入了撤离名单。但是,一个单身母亲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其中一位还坐着轮椅,怎么能在战区的中心到达那里呢?
“有很多步骤,非常困难,”她说。“而且非常危险。”
找到交通工具是第一个挑战。他们本来打算在上午9点出发,但两小时后才找到唯一可用的交通工具:一辆由朋友安排的破旧车辆。他们一直走到Salah al-Din高速公路,这是一条从北向南的主干道。
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辆驴车,把他们带到以色列检查站。
他们和其他数百人一起步行经过,在轮椅在路上坏掉的时候,他们慢悠悠地走了一个小时。两名年轻的加沙男子自愿抬着仍然坐着的祖母,直到他们到达以色列国防军的停靠点。其他年轻人被从人群中拉出来,然后消失了。军队人员让家庭在混乱中分离,让他们逃跑;老年人摔倒并被抛在后面。
尸体散落在道路两旁。
珍妮特回忆起在检查站,他们和其他所有人被要求跪在一个被炸毁的弹坑里,珍妮特把一块白布举过头顶。一辆推土机正在他们面前倾倒沙子——可能是为了制造安全屏障——但孩子们认为他们会被活埋。四个小时后,他们都获准继续向南行进。
珍妮特说她很幸运有现金叫出租车。她花了500谢克尔(133美元),花了通常30谢克尔(8美元)20分钟的车程,却发现边境已经关闭。幸运的是,司机愿意把他们送到六英里外汗尤尼斯的癌症医院。
附近的旅馆没有房间,但因为祖母是病人,医院允许这家人呆在候诊室。经过一个不眠之夜,珍妮特的哥哥打电话给当地的一个穆斯林朋友,叫了另一辆出租车去拉法边境。
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好消息和坏消息。珍妮特和孩子们的名字被贴在墙上的出境名单上。她父母的名字却没有。珍妮特说,虽然土耳其提交了他们的名字,但以色列尚未处理癌症患者的转移。她发现,在过去的某个地方,她的母亲丢失了她的手机,她让她的哥哥安排父母住在当地的某个地方。
除了把珍妮特的手机留给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了。
图片:Hanna Maher提供
马赫一家团聚了。
在边境的另一边,汉纳焦急地等待着,再也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周五,他已经在拉法逗留了一整天,但保安人员告诉他,作为一名牧师,在这里过夜不安全。西奈半岛历来是萨拉菲穆斯林地下极端组织的温床。
汉娜向西走了30英里来到阿里什,第二天早上又回来了。
当外国护照持有人提交他们的文件时,在过境点内有大量的人。数十名使馆工作人员等在另一边,准备迎接他们。汉娜说,珍妮特和孩子们是第一批离开的埃及人,因为教会已经跟进了她的案件。
珍妮特说:“办公室里有人告诉我:有很多人打电话问你的事。”“但是那些没有人帮助的人怎么办?”
当他们离开时,汉纳看到人群中有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但他们是如此憔悴和苍白,直到他们走到大约15英尺远的地方,他才认出他们是自己的孩子。然后他笑了,到处拥抱。
但仍有工作要做。汉娜参加了由政府协调的向加沙南部巴勒斯坦人伸出援手的活动,这些巴勒斯坦人从拉法离开,汉娜和珍妮特一起给那些在避难所瑟瑟发抖的人送去了一些毯子。他们的出现引起了惊奇和一丝恶意。
你怎么能接受一个没穿衣服的女人的帮助?一个人问他的朋友。其他人感到震惊,但不愿意接受基督徒的援助,把他们与以色列和美国的行为等同起来。
沿着地中海向西走了90英里,珍妮特终于和家人在伊斯梅利亚的汉娜姐姐家休息了一下,那里位于苏伊士运河以南40英里处。她在那里哭了,想着那些还在圣波菲利斯教堂避难的人。
现在,终于回到开罗的家,她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那我弟弟和妹妹呢?”珍妮特问。“他们怎么出去呢?”
起初,社区有很大的决心留在原地,等待战争结束。珍妮特说,有消息说,希腊东正教主教告诉以色列国防军,他不会是清空加沙基督徒的人。他们的教堂是以四世纪向当地异教徒传福音的圣人命名的。
来自天主教庇护所的一个声音具有象征意义。
塔拉齐说:“我们不接受流离失所者离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教堂。“我绝不离开教堂,除非进了坟墓。”
珍妮特说,但大约两周前,随着食物和燃料开始耗尽,她的情绪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随着消息传到世界各地,一些人建议以色列促进基督教运动到约旦河西岸——那里有许多加沙人的亲戚。
马萨德说:“即使以色列同意,这也会使基督教社区在穆斯林邻居面前显得不好。”“但我开始改变主意了。”
在与教会长老交谈后,他自己作为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决心动摇了。
然而,在约旦河西岸,杰克·萨拉餐厅却没有。
“基督徒是巴勒斯坦人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伯利恒圣经学院院长说。“作为一个社区,他们从来没有受到过自己人的威胁,我怀疑他们想要得到特殊待遇。”
这样做会破坏信任、社区和平和福音见证。萨拉说,如果以色列真的想帮助他们,就让他们回到他们被驱逐到加沙之前的家园,回到雅法、马吉达勒和贝尔谢巴等以色列城市。
以色列转而要求阿拉伯和西方国家接收加沙难民。
珍妮特把这种情况比作但以理在狮子坑里的夜晚:上帝在保护他们,但还没有把狮子赶走。她明白如果基督徒受到特殊待遇会有什么问题,也明白加沙没有基督教的问题。
但她说,人们已经绝望了。她的祈祷是战争能停止,她说这也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她也祈祷她的母亲能去土耳其——现在,她的母亲终于通过了大使馆的手续。
如果她祈求和平的祈祷失败了,她请求上帝让基督徒离开。
珍妮特说:“即使我们没有死于以色列的轰炸,我们也会死于缺乏食物和药品。”“加沙的基督徒想要离开,无论他们要去哪里。”
编者按:在其他八种语言中,现在有阿拉伯语的部分CT的以色列-哈马斯战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