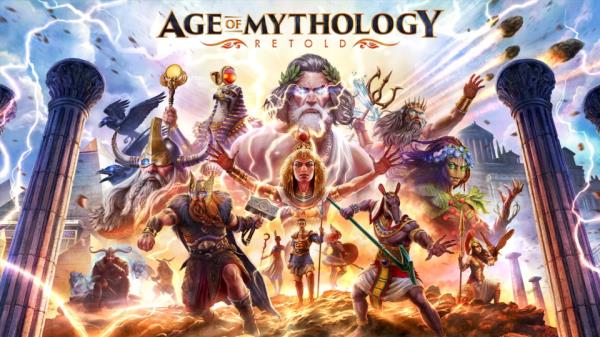今年5月,路易斯维尔警方接到了一起针对一名名叫利特森·佩雷斯-加兰的男子的家庭暴力投诉。一名警官写道,受害者是佩雷斯-加兰孩子的母亲,“她说自己抱着孩子坐在床上,罪犯打了她的左脸。”“然后,受害者让婴儿坐在床上,受害者说,罪犯把她带到浴室,再次打她的脸,然后开始打她的肋骨区域。受害者的左脸有红色的伤痕,嘴唇上有一个小裂口,下巴附近疼痛。”
刑事司法系统——一个经常忽视或低估家庭暴力的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佩雷斯-加兰受到了限制令的限制。它禁止他接近所谓的受害者500英尺内,也禁止他与她联系。
此外——这也是本专栏的主题——该命令禁止佩雷斯-加兰持有枪支。
下个月,佩雷斯-加兰在德克萨斯州靠近墨西哥边境的地方驾驶一辆18轮货车时被拦下。在他的背包里,有一支偷来的西格绍尔手枪;在他的钱包里,有一份法庭命令的副本上面写着他的释放条件。他被指控违反了一项联邦法律,该法律禁止家庭暴力限制令下的人持有枪支。
到目前为止还好吗?在最高法院今年对纽约州步枪和手枪协会诉布鲁恩案做出裁决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六名法官组成的保守派多数派否决了纽约州的隐蔽携带许可法,他们表示,枪支监管必须基于或类似于历史上存在的那些法规,才能通过宪法的审查。在没有历史先例的情况下,枪支法违反了宪法第二修正案。
你也许能猜到这是怎么回事。事实证明,在殖民时代及以后,当局并没有认真对待家庭暴力。因此,佩雷斯-加兰的律师做了律师该做的事:他抓住布鲁恩的机会,辩称该法律侵犯了佩雷斯-加兰的第二修正案权利。
律师谢恩·奥尼尔(Shane O 'Neal)写道:“美国独立战争确保了白人男性的权利,他们的私人事务不受政府的干涉。”他认为,独立战争之后,“新成立的美国脱离了英格兰和新英格兰殖民地惩罚家庭暴力的法律。相反,保护妇女和儿童不受男户主虐待的做法被抛弃了,因为它们与新确立的家庭神圣性不相容——家庭是不受政府干预的私人领域。”他引用了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法庭显然不愿意对男性虐待家庭家属的行为施加约束。”
这一点也不奇怪:由于家庭暴力不被视为一个问题,没有太多证据表明开国时代的规定禁止被控者持有枪支。奥尼尔说:“我们的缔造者绝不会想到解除那些被指控但未被判家庭暴力的人的武装。”
没错:因为当时的法律是支持虐待妇女的,所以它现在不能被解释为保护她们。
积极为他的当事人辩护是奥尼尔的工作。忠实而合理地解释宪法是法官的工作,而这正是事情真正偏离轨道的地方。美国地区法官戴维·科斯(David Counts)本月裁定,这项联邦法律违反了宪法第二修正案,并下令撤销对佩雷斯-加兰的起诉。
“家庭施暴者并不是新事物,”最初由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提名并由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重新提名的Counts说。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政府对家庭暴力的干预——更不用说没收个人的枪支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从殖民时代到1994年的历史记录中,明显没有从被指控(甚至被判)家庭暴力的人那里没收枪支的一贯例子。”
这就是最高法院所做的,它疯狂地关注原始主义,甚至更加狭隘地坚持,对“原始公共意义”的追寻必须仅限于对历史类似物的寻找。尽管开国元勋们并没有想到用3D打印机生产鬼枪,也没有想到扩展版杂志——也没有想到妇女的权利,就这一点而言。
这有多荒谬?伯爵列举了历史上对殴打妻子的惩罚:在1672年的一起案件中,一名男子被判处“十鞭鞭刑”,或者是根据19世纪70年代加州刑法的一项规定,虐待配偶者“后背要挨不少于21鞭”。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是最顽固的原始主义者也会得出结论,根据第八修正案,现代的鞭笞法构成了“残忍而不寻常的”惩罚,无论当时发生了什么。
布鲁恩的余震刚刚开始影响下级法院;Counts的裁决可能不会成立。即使在高等法院对枪支管制的勉强态度下,也有可能维持这一限制。Bruen的法院强调,第二修正案保护“普通、守法的成年公民”在家庭之外携带枪支的权利。一个人因为攻击亲密伴侣而被捕,并受到法官发布的保护令,他既不普通——让我们希望如此——也不守法。而且,正如司法部在佩雷斯-加兰案中所主张的那样,第二修正案是“在允许解除危险人士武装的历史背景下通过的”。
但布鲁恩核泄漏的证据令人担忧。上个月,纽约的一名联邦法官宣布布鲁恩枪击事件后通过的一项州枪支法无效,该法律限制夏令营等地的枪支;他的理由是殖民地时期没有这样的营地。去年9月,科斯推翻了一项联邦法律,该法律禁止那些被指控犯有重罪但尚未定罪的人持有枪支。他承认:“对于这起案件的现实后果,没有任何幻想——当然,有效的公共政策和安全担忧是存在的。”然而,布鲁恩把这些担忧仅仅当作一种历史分析。本法院遵循这一框架。”
我在夏令营判决后写道,这是“模仿的原创主义”。但这低估了形势。这是原始主义的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