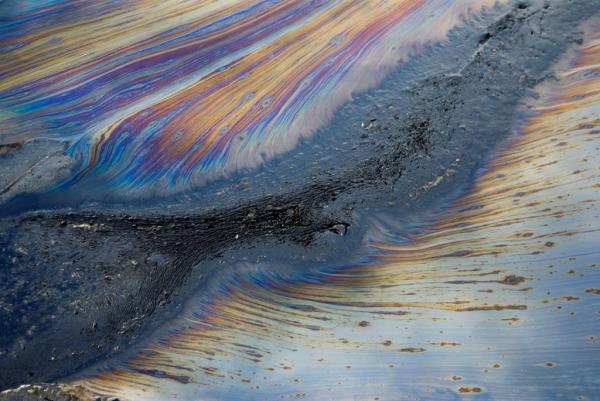盯着伟大的西班牙艺术家Diego Velázquez画的脸看多久都不会产生任何清晰的表情感。胡安·德·帕雷哈(Juan de Pareja)是1650年这幅肖像画中的非裔西班牙人,他既没有微笑,也没有皱眉。他的眼睛闪闪发光,直视着观众,没有一丝爱意、敌意、好奇或不耐烦。如果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百叶窗是紧闭的。了解他个性的唯一清晰线索是他的智慧。
帕雷哈也是一名艺术家,她是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一个规模不大但颇具影响力的展览的主题。在Velázquez画他的肖像之前的几年里,帕雷哈一直是Velázquez的奴隶,在他的工作室里为他服务,并陪同他旅行。在Velázquez画出这幅著名的深色皮肤的英俊男子形象后不久,帕雷贾在再服务四年后获得了自由的承诺。这次名为“胡安·德·帕雷哈:非裔西班牙裔画家”的展览,是帕雷哈1654年之后的首次作品展,从那时起,他在法律上、个人上和艺术上都独立于他的主人。
一张无表情的脸是它自己的一种表情,是对脆弱的拒绝,是对观者情感洞察力的下降。这是一个面具,在这种情况下,几乎可以肯定,它隐藏了两个艺术家之间复杂而充满情感的关系,一个正在冉冉升起,另一个当时正在匿名工作,可能是在复制Velázquez最受欢迎的作品。看着这幅画,对自己说:“他在看着拥有他的人。”面具很有意义,但一个人每天每时每刻都戴着它要花多少钱呢?
在阿姆斯特丹,一场千载难逢的维米尔画展
这幅画是在罗马制作的,它生动、人性化地描绘了一个具有非洲特征的男人,引起了轰动。这是西班牙艺术家在罗马精英中的名片,在这次展览中,它与另一幅同样令人惊叹的Velázquez教皇英诺森十世的肖像相对。
1971年,大都会博物馆大张旗鼓地获得了帕雷贾的画像,很可能获得了Velázquez为教皇画像的权限。在同一个房间里看这两件作品是一种爆炸性的体验。社会等级的两端都由一个复杂的协会链来代表和联系。
帕雷哈的奴役经历进一步推动了Velázquez的成功,而这幅被奴役的黑人的画像也促成了对欧洲最高权力人物之一的描绘。Pareja克制着自己的情感和接触,而Innocent X则毫无保留,抿紧嘴唇,露出一丝嘲讽,一双炯炯的眼睛几乎在喊“走开!”的问题。
这次展览的大部分内容都集中在阐释17世纪西班牙多种族社会的复杂性上。奴隶劳动和对美洲的殖民剥削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奴隶制深深植根于西班牙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中。
在塞维利亚,工匠阶层依靠奴隶劳动来生产奢侈品。在政治和宫廷生活的中心马德里,奴隶制是地位的象征。当Velázquez将被奴役的Pareja带到罗马时,在那里奴隶制不那么普遍,当地人可能会觉得一个艺术家带着人类的财产四处游荡有点古怪或炫耀。
一位伟大的威尼斯艺术家在国家美术馆得到了应有的赏识
奴隶制的种族化深深植根于美国丑陋的历史,但在西班牙却没有那么根深蒂固。当帕雷哈作为一个自由人和独立艺术家出发时,他在马德里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画的是天主教主题,尽管教会接受奴隶制。在西班牙复杂的历史中,种族主义和种族思想包含了对犹太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人口混合的深切焦虑。
不幸的是,这次展览被安排在了大都会博物馆罗伯特·雷曼收藏馆(Robert Lehman Collection)的侧翼,这是这座大楼里最不和谐、最脱节的几家画廊。这样一来,就不可能将Velázquez的贵族肖像(包括帕雷贾的肖像)与附近走廊上摆放的迷人而感人的作品(包括非洲人后裔)放在一起。
这些由不同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包括Velázquez的三幅厨房女佣的相关图像,以一种真正的洞察力和同理心描绘了仆人阶级的黑人。就像Velázquez图片中的女仆一样,在穆里略动人的《三个男孩》中,一个黑皮肤的男孩也戴着一个面无表情的面具。如果把它们放在离帕蕾哈画像更近的地方,也许会有一些启示。作为一个被时尚艺术家奴役的人,帕雷贾看到了罗马,这几乎肯定扩大了他艺术视野的广度;无论是被奴役的还是自由的仆人,看到的世界要少得多。
Pareja自己的作品大多被放置在另一个走廊空间,这也是不幸的。在优秀的目录中,联合策展人大卫·普林斯(David Pullins)确定了14件属于帕雷哈的作品,其中5件在展览中展出。
如果有更多就好了,但这次展览包括两幅可能是他全部作品中最重要的宏伟画作。《圣马太的召唤》(1661)和《基督的洗礼》(1667)打消了任何挥之不去的想法(在研究帕累哈的学者中更为普遍),即他是一个次要的Velázquez。它们是规模宏大、奇特的巴洛克杰作,有着复杂的戏剧和几何形状,对细节的关注。
它们强调了普林斯和他的联合策展人凡妮莎·k·瓦尔德萨梅斯(Vanessa K. valdsamas)的一个更大的论点,即帕雷哈在奴役后的作品与Velázquez精致、敏感和宫廷的美学有所不同,而更多地是对马德里画派画家的丰富和色彩的同情,这些画家在17世纪中叶的马德里创造了一种新的风格。
帕雷哈的另一幅作品《飞往埃及》(The Flight Into Egypt, 1658年)笨拙而令人腻味,也许是对马德里画家作品的一次不成功的个人尝试。圣马太和洗礼画表明一个完全完整的过渡到一个独立的视野。
事实上,展览中有两幅帕蕾哈的肖像。第一个是Velázquez,是最有名的。第二幅是帕雷贾的自画像,他把它放在最左边,和其他人物一起,放在他的《圣马太的召唤》里。毫无疑问,他们是同一个人。在《圣马太》的画布上,帕雷哈描绘了另一位来自马德里画派的画家何塞·安托利内斯站在他旁边——这标志着这位曾经被奴役的艺术家现在融入了更大的艺术圈子。
你从未听说过的最伟大的鸟类艺术家
在他的自画像中,帕雷贾再次直视着观众,他的嘴也没有流露出任何情感。但他右眉上方的一小块光线暗示了一丝讽刺,为Velázquez这张迷人的智慧照片增添了一丝自信。帕雷贾确实在画面中,但与戏剧无关。他和安托利内斯只顾着自己,有点像舞台管理人员,他们看了太多的演出,不再需要太多的关注。
这是什么意思?有时候,在艺术中,人们看到的东西很有意义,很重要,很能引起共鸣,但却没有具体的意义。我能想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帕雷贾在说:“看看我做了什么。”但他不肯告诉我们他指的是艺术品还是他自己。
胡安·德·帕雷哈:非裔西班牙裔画家:至7月16日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metmuseum.org。